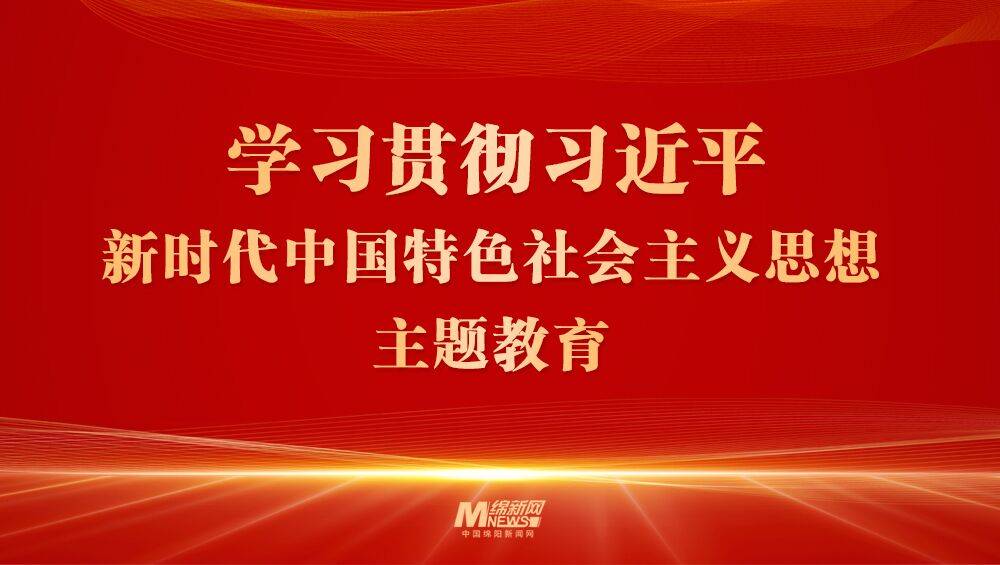□ 李敏
夏日驕陽下,涪江、安昌江與芙蓉溪交匯處的水面格外明亮,似盛滿熔金的河流奔涌向前。我沿江畔行走,感受被江水沖刷出的古城生命痕跡,目之所及,皆如潑墨畫卷,延展著歲月與生命本身的故事。
涪城是被三江托在掌心的城。站在越王樓俯瞰,三條江水各攜姿態奔來:涪江最壯闊,像穿青布長衫的漢子,裹著上游雪山的清冽,浩浩蕩蕩撞入城區;安昌江溫婉,水面泛著細碎鱗光,像裹著素色綾羅的女子,貼城郭邊緣輕移蓮步;芙蓉溪最纖巧,繞東山腳邊打個彎,才羞答答匯入主流。它們在交匯處輕擁,水面漾開的漣漪,竟似不忍分離的吻。江風裹著水汽撲在臉上,混著岸邊綠樹的清香,潮濕溫潤里藏著草木微澀。
江上橋身姿各異。東方紅大橋沉穩厚重,橫臥江面任流水日夜穿身而過;富樂大橋柔緩的弧線劃破水面,如一道臥波長虹;三江大橋則讓人窺見奇景——三條“巨龍”并肩跨江,靜臥波光之上,又似年歲懸殊的兄弟,默然相守。
行至鐵牛廣場,鎮水鐵牛正臥于其間。青灰色鑄鐵身軀上,水銹如老墨洇染,四肢緊繃的肌肉線條里,仍凝著當年工匠澆筑的溫度。涪城老人常說,傳說有一年涪江發大水淹沒半座城,知府請鐵匠鋪老師傅帶二十個徒弟,在江邊燒了三個月鐵,才鑄出了一頭“鎮水神牛”。如今,新鑄的鐵牛犄角仍朝江面,江水卻早已馴順——汛期來時,遠處橡膠壩緩緩升起,輕輕按住浪頭。古人以鋼鐵寄愿,今人以智慧安瀾,涪城與水的相處之道,全刻在這鐵與水的對視里。
濱江綠道如翠帶垂岸。樹蔭長廊中,游人緩踱,跑者攜風疾馳;長椅上,幾位老人搖蒲扇閑話。江水在堤下奔涌,與林蔭道的市聲相融,人行走其間,竟似被夾在兩道奔流中:頭頂樹聲簌簌,腳下水語潺潺,生命便在這流動的聲浪里,不絕地向遠方延展。
暮色漸沉,江水披上朦朧輕紗。我獨坐長椅,看兩岸燈火次第點亮,浮于江面恍若星河傾落。遠處霓虹勾勒城市輪廓,近處廣場成了光的海洋:音樂乍起,舞者身影在光影中躍動,連白發都煥著青春;鐵牛廣場上,胡琴聲起,婉轉唱腔引得游人駐足。一江靜水,倒映著人間萬家燈火。
賣冰粉的阿姨推著小車走過,掀開木蓋,紅糖甜香漫開:“先生,要碗冰粉不?加醪糟的,綿州老味道。”我接過碗,冰涼瓷碗貼著掌心,紅糖水里的冰粒咯吱作響,混著遠處廣場舞的音樂,把白日燥熱一點點澆散。
日已暮,游人大多歸去。廣場下的河邊,點點夜光漂在暗沉水面上,如銀河抖落的微星。有人端坐小凳,有人背靠鐵牛,于萬籟俱寂里側耳聽水的喘息。
歸途上,江水絮語愈清。訴說著鐵牛鎮水的傳說,道古渡號子的回響,講新橋通車的歡慶,也念此刻岸邊戀人的呢喃。這江水從雪山來、向東海去,卻在涪城留下最溫柔的臂彎。千百年來,它沖刷城墻、滋養生計,帶來過驚濤,也孕育過繁華。
望著這萬古流淌的江水,我忽然懂了何為“逝者如斯”。那份被江水撫慰的感動,終將永恒如新。待晨曦微露時,它又會把涪城的倒影,溫柔揉碎在粼粼波光里,一如往昔,一如未來。